大模型是我们时代的印刷术吗?

Henry Farrell等 本文作者
彭晨 本文编译
本文转载自“集智俱乐部”
大模型正重塑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态,但其本质常被误解。《Science》上的一篇最新文章,揭示大模型并非自主智能主体,而是一种革命性文化社会技术,类似于语言、印刷与市场制度。它以独特方式汇聚并重构人类信息,成为“人类社会人工系统”的新变体。这一重新定位的理论框架引导我们超越“机器接管”与“乌托邦助手”的狭隘辩论,转而关注更为现实且紧迫的问题:大模型将如何影响资源分配、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以及权力结构的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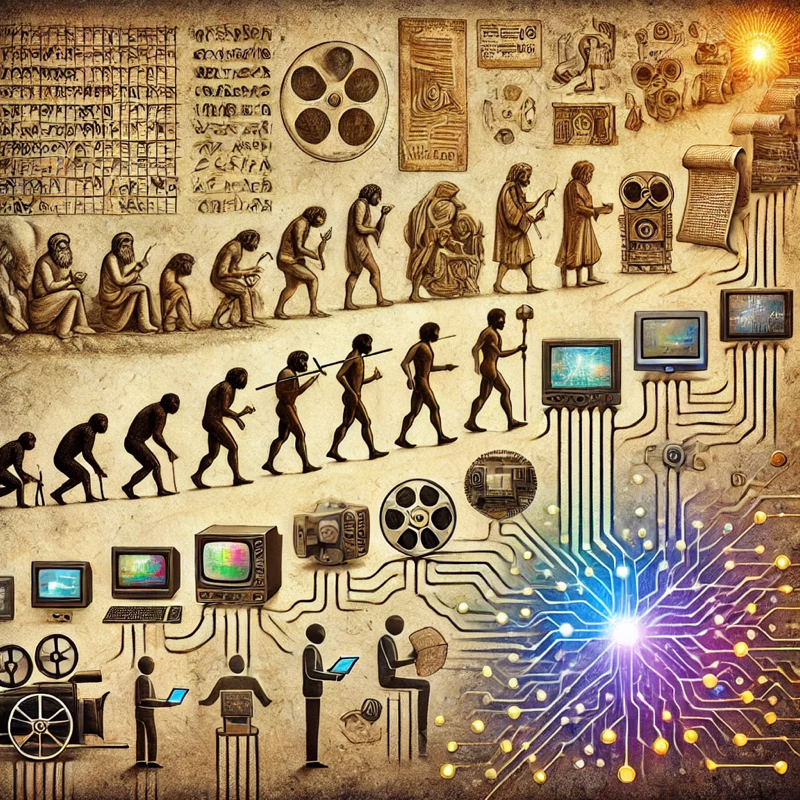
大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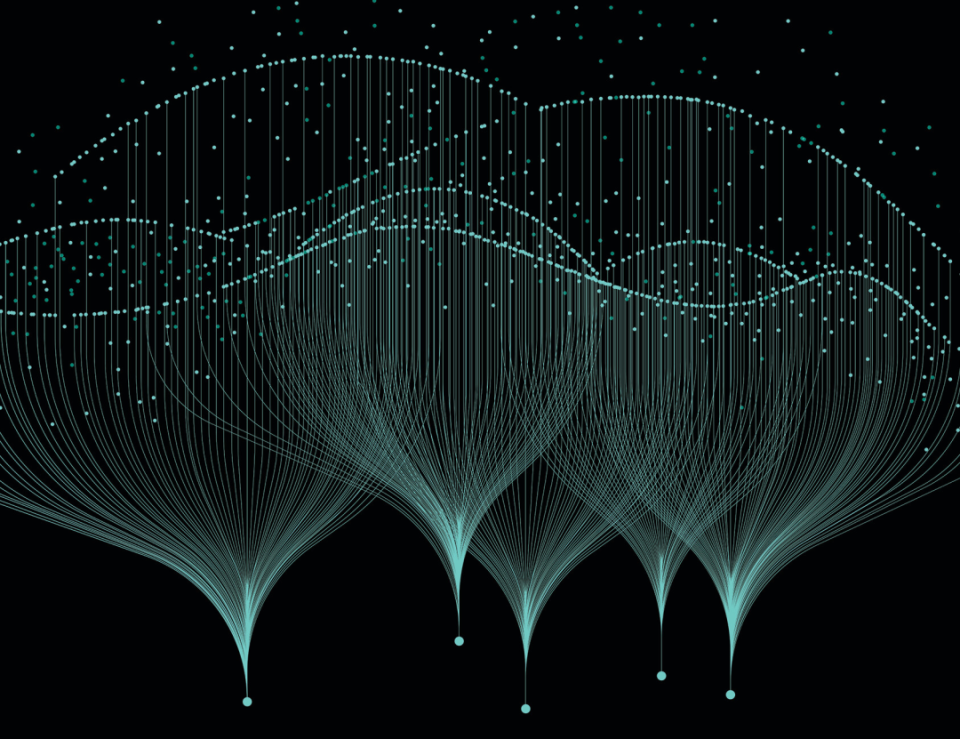
挑战与机遇

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来源:
[1] H.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MIT Press, 1996).
[2] F. A. von Hayek, Am. Econ. Rev. 35, 519 (1945).
[3] J.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 Press, 1998).
[4] D. Davies, 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Univ. Chicago Press, 2025).
[5] E. Yiu, E. Kosoy, A. Gopnik, Perspect. Psychol. Sci. 19, 874 (2024).
[6] T. Chiang, New Yorker 9 (2023).
[7] C. Goldin, L. Katz, Q. J. Econ. 113, 693 (1998).
[8] D. Acemoglu, S.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 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Hachette, 2023).
[9] M.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Duncker & Humblot, 1919).
[10]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gmans and Green, 1920).
[11] L. Hong, S. E. Pag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1, 16385 (2004).
[12] S. Lai et al., Proc. 41st Int. Conf. Mach. Learn. 235, 25892 (2024).
[13] J. Sourati, J. A. Evans, Nat. Hum. Behav. 7, 1682 (2023).
[14] S. L. Blodgett, S. Barocas, H. Daumé, H. Wallach, arXiv:2005.14050 [cs.CL] (2020).
[15] L. Brinkmann et al., Nat. Hum. Behav. 7, 1855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