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来模式揭秘:GLP-1,AI加速药物发现,礼来如何突破创新者窘境?
编译:Ivy、Haozhen
在深刻变革且日益艰难的美国医疗环境中,新药的研发与商业化正遭遇多重结构性阻力:监管持续收紧、临床试验成本高昂,而仿制药体系在压低价格的同时又造成质量不稳与供应脆弱,医疗支付端则长期存在定价扭曲与激励错配。在这样一套高度摩擦、效率受限的体系中,要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变得愈发困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拥有百年历史的礼来仍然实现了跨周期的跃迁:从胰岛素时代迈入 GLP-1 时代,在科学突破与商业模式上都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长的曲线。如今礼来市值逼近万亿,已大幅领先其他制药公司,而推动这一跃升的核心力量正是突破性的 GLP-1 药物。它不仅在糖尿病与肥胖领域带来革命性效果,也在心血管健康、炎症控制与成瘾行为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潜力。
但礼来的成功并不限于药物层面,更体现在它对行业结构性问题的深刻理解:通过 LillyDirect 打破 PBM 主导渠道、以直连患者的方式降低摩擦;通过 AI 重塑药物发现流程、提升早期研发效率;通过组织结构创新,在外部生态与内部研发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方式等。
本文基于 Stripe 与礼来 CEO 的对话,对公司在研发体系、商业模式转型、AI 带来的结构变化,以及美国医疗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01.
GLP-1:礼来近万亿市值的秘密
礼来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制药公司,CEO Dave 认为公司市值高的原因在于:
1. GLP-1 药物的巨大价值:这类药物可能贡献了公司约 80% 的价值。礼来正处于 GLP-1 早期增长阶段,有很大增长空间,今年截至目前的收入增长率已达到 40%。在美国新患者市场中,礼来的市场份额约为 70%-75%。
2. 市场对研发投入的信任:华尔街对礼来公司每一美元的研发或收购投入都给了额外的溢价,这反映出投资者对礼来研发生产力的高度信心。
3. 自费潜力与品牌价值:市场普遍认为 GLP-1 所开启的周期与以往不同,这源于全球对健康的强烈需求,许多人愿意自费购买有效药物。礼来有潜力在市场渠道和消费者端建立自费(self-pay)品牌业务,使特许经营价值超越专利周期。虽然礼来尚未形成类似苹果的生态系统,但这种潜力是支撑礼来高估值的重要因素。

GLP-1 是什么?
当我们进食时,身体会启动一系列代谢反应,例如产生饱腹感、让脂肪细胞吸收游离脂肪酸、促使肝脏释放糖原等。其中最关键的调节者是胰岛素,而胰岛素的分泌主要受到一类称为“肠促胰岛素”(Incretins)的激素激发。
1971 年有研究首次证明了所谓的“肠促胰岛素效应”:相比将相同剂量的糖直接注入静脉,通过消化道摄入糖分会让胰岛素反应更快更强,说明肠道在摄入食物后会释放额外的代谢信号。
随后,研究者明确了两种主要的肠促胰岛素激素:GIP(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多肽)和 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 -1)。不过,这些天然激素本身并不适合作为药物使用,因为它们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极短,例如 GLP-1 只有大约五分钟。如果直接使用未改造的天然蛋白,患者几乎需要全天持续输注才能维持疗效,这在临床上无法实现。
因此,现代制药公司通过分子工程延长这些激素在体内的存在时间,让激素不易被分解,从而发展出每天甚至每周注射一次即可维持稳定效果的方案。礼来公司在 20 世纪率先大规模生产胰岛素,如今凭借新型 GLP-1 糖尿病和减肥药成为市场领导者。
• 药物效果
GLP-1 药物之所以能帮助减重,关键在于它能让人减少每日热量摄入,并克服身体在减重时出现的反弹机制。从数据来看,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约 3600 卡路里,而服用 GLP-1 后平均能减少约 800 卡路里,相当于少吃一顿饭。更重要的是,药物能抑制体重下降时出现的强烈饥饿感,以及高胰岛素血症引发的反向调节反应,使减重过程更稳定,也减少情绪负担。

GLP-1 工作原理
• 如何推广 GLP-1?
尽管 GLP-1 药物在减重和代谢改善上效果显著,目前的使用规模仍然有限。美国约有 1000 万人正在使用 GLP-1,但肥胖人群高达一亿人,渗透率仍然偏低,这主要受保险覆盖不足和医生时间有限的制约。
但目前推动市场增长的力量正逐渐发生变化:自费购买成为最重要的增长来源之一。虽然每月费用高达 500 美元,但很多人仍愿意支付。比如 Zepbound 的自费新患者数量不仅超过了保险覆盖的新增患者,也超过了所有 Wegovy 的销量,说明只要成本效益合理,消费者会愿意主动承担预防性治疗的部分费用。
Zepbound:一种由 Eli Lilly 推出的每周注射处方药,活性成分为 Tirzepatide,适用于成人肥胖或超重患者,用于减重并维持体重,同时需要配合低热量饮食与增加活动量。
Wegovy:一种每周注射的处方药,活性成分为 Semaglutide,为成人肥胖或伴有体重相关医疗问题的超重人群提供体重管理,并可减少心血管事件风险,需配合减肥饮食和锻炼。
在营销策略上,礼来已将 70% 的预算从电视等传统渠道转向搜索和 GenAI 优化。不过,面向医生的广告推广仍然非常重要,因为有推广支持的医学发明的普及速度通常是缺乏推广的同类发明的两倍。
从供给角度看,如果未来要扩大 GLP-1 的供给,关键在于口服剂型的推出。目前注射剂产能受限,难以覆盖全球庞大的潜在患者群体。口服药效力可能略低于多重作用的注射剂,但一旦获批,它们将成为长期维持治疗的重要形式。随着仿制药上市,GLP-1 预计将覆盖超过 4000 万成年人,规模将超过当前使用他汀类药物的人数。
虽然 GLP-1 药物在长期能降低整体医疗成本,但报销依旧困难,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和雇主普遍关注短期预算,难以承担前期费用。这种“短期成本 vs 长期收益”的错配,是所有预防性药物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美国医疗体系存在典型的“既得者问题”:新药往往面临最严苛的审查,但已有的服务和项目却几乎从不被重新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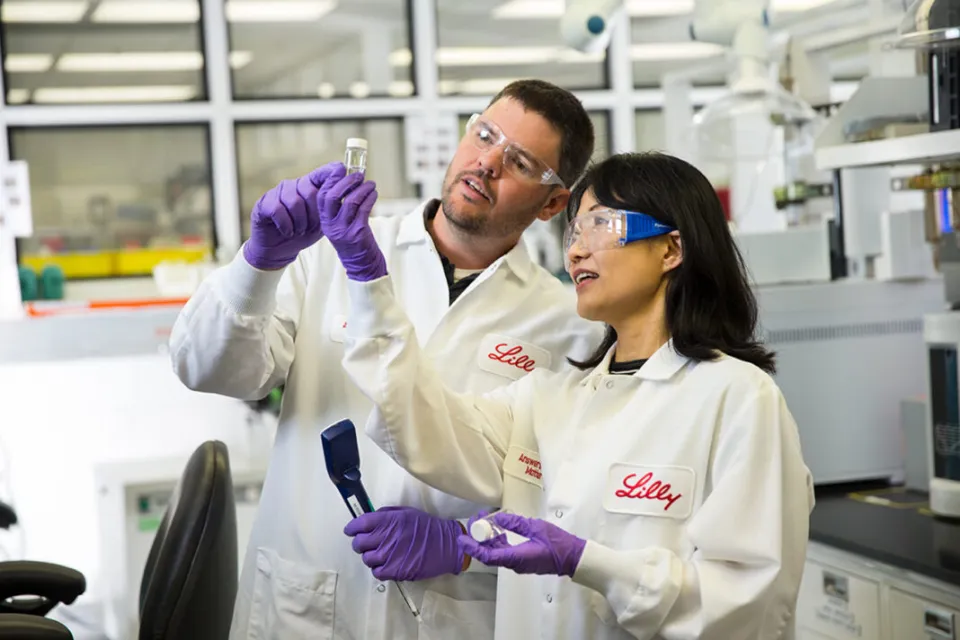
02.
AI 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与局限
今年 10 月,礼来公司在 GTC 大会上宣布与 NVIDIA 合作,计划在年底前建成一台本地超级计算机,用于运行公司专有的药物发现模型。这台计算机被认为是目前最大、以生物学为核心的系统,同时也是使用 B300 最新芯片构建的最大平台。科学家们将利用它进行新药发明和联合开发,初期重点聚焦化学领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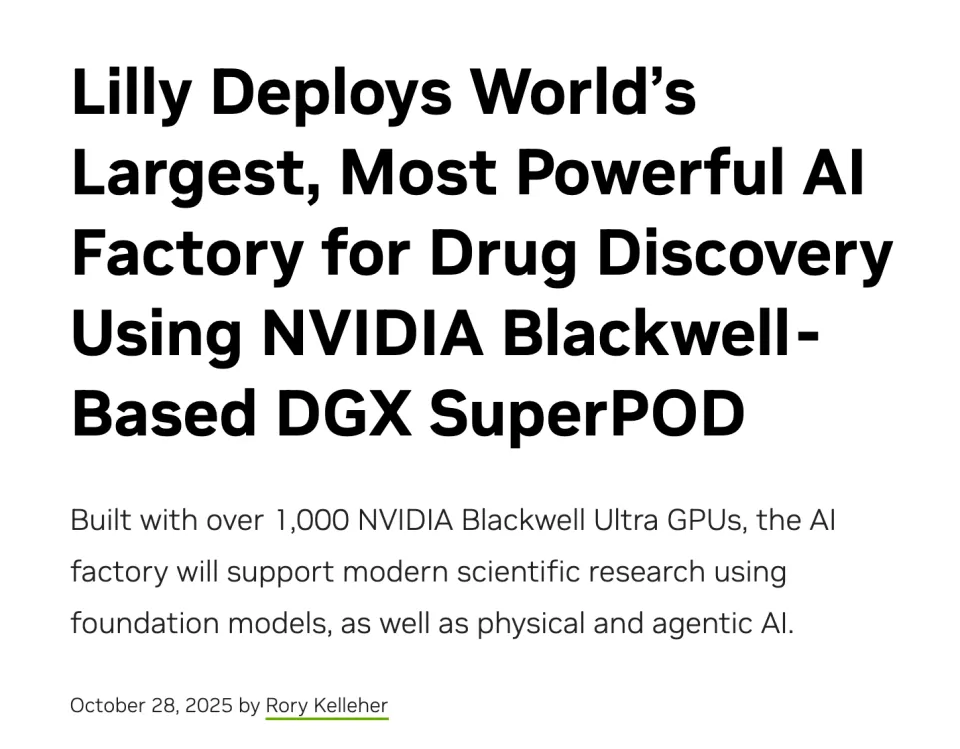
在药物发现中,人们正在尝试让 AI 用微小化学物质模拟大型蛋白质,例如 GLP-1 激素肽与 G 蛋白偶联受体的作用。这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任务,需要新物质只产生预期效果。AI 通过预测非自然的原子排列和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些结构在自然界中不存在,但可以有效作用于靶点。完全由 AI 驱动的药物尚未进入临床,但相关成果正在逐步出现。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 AI 在解决生物医学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被高估:
1. 靶点选择本身极为困难,AI 的辅助作用有限;
2. 许多药物在人体毒性阶段仍会失败,而 AI 对这一环节的帮助不足。
礼来认为,要真正克服这些挑战,AI 模型必须依赖更完整的生物学知识库进行训练。目前,人类对生物学的了解估计仅有 10% 到 15%,只有当这一比例显著超过 50% 时,AI 才能有效处理大型系统的预测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全天候机器人实验生成训练数据集,而在美国,这项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03.
礼来如何研发、销售药物?
礼来研发投入已接近国家级机构水平
研发是礼来的核心业务,占公司整体的约 80%。为了维持这一核心驱动力,今年公司的研发支出预计将达到销售额的 20%–25%,总额约 140 亿美元,规模已接近国家级科研机构(如 NIH)的投入水平。
从数据上来看,开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高达 35-40 亿美元,其中超过 60% 来自最关键也最昂贵的三期临床试验,每年消耗逾 10 亿美元。当前每位用户在购买 GLP-1 药物所支付的费用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流向了科研实验室和临床试验体系。
从研发路径上来看,礼来早期研发围绕两条路径展开:
1. 平台创新:公司会探索是否存在一种全新的技术或方法,能够以更高效或更具突破性的方式作用于已知靶点,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药物开发领域。这类投入规模大、周期长,本质是提前押注一场可能改变行业的浪潮,因为一旦错过早期阶段,后续机会几乎不复存在。像 Genentech 借助单克隆抗体实现突破,或 Gilead Sciences 在病毒学化学和小分子药物上建立优势,都是这种路径的典型案例。
2. 靶点选择:在广阔而复杂的生物发现空间中,公司会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挑选少数高度相关的靶点,并围绕这些靶点组织团队开展药物探索。礼来会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小分子、抗体或 siRNA 等多种技术工具,以提高找到可行药物的概率。例如在 Lp(a) 项目中,公司最终确定了小分子和 siRNA 两条路线,目前都已进入三期临床。
除了内部研发外,礼来还在搭建一个覆盖更广的创新生态。公司通过企业风险投资,并设立诸如 Catalyze 360 和 Gateway Labs 等平台,吸引具备规模化潜力的公司入驻。在这些平台中,礼来提供技术服务与专家支持,帮助解决具体的研发难题。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松散耦合的合作结构:礼来并不试图把研发全部抓在自己手里,而是借助外部的资金、人才和创意来推动创新。

如果在早期阶段错过机会,公司通常会选择在周期的后期通过收购补位,并利用自身在临床试验、制造与规模化方面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
在 Dave 看来,美国新药与新分子实体的诞生正越来越多由生物技术公司主导,约三分之二的创新来自这些更灵活的企业,而非传统制药公司。因此,制药公司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它们更像是管理大型投资组合的私募股权经理:从全行业视角审视趋势,押注潜在赢家,并在后期负责扩大规模和推动全球分发。而真正承担高风险创新的,往往是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支持的早期团队。
礼来认为行业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研发模式的公司:
1. 由小公司成长而来的生物技术企业,它们自身保留较强的研发能力;
2. 将早期研究几乎完全外包、专注于临床试验推进的公司。
而礼来的选择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模式,通过保留内部研发能力,同时积极开展外部合作、收购与投资,在内部创新与外部创新之间取得平衡。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在于:
1. 在药物发现阶段,规模不是优势,因为这一阶段本质上需要更分散、灵活的探索方式。因此,礼来在圣地亚哥建立了一个 400 人规模的单克隆抗体中心,以“小公司模式”运行,但同时免去了融资与市场波动的压力,从而保持专注与灵活。
2. 药物进入开发后期后,规模优势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在临床试验、全球生产还是分销方面,大型公司都往往比小型生物技术企业更快、更可靠,也更具成本效率。虽然过去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新药来自生物技术公司,但这些公司往往难以独立完成后续开发,因为临床阶段的资金压力与风险巨大,而风险投资基金通常不愿意承担这些成本。
LillyDirect:DTC 模式改变药品供应方式
过去,礼来与患者的关系主要依赖药房等中间商,但这一格局随着 LillyDirect 的出现开始改变。
LillyDirect 是礼来在美国推出的 “直接面向患者” 数字化健康平台,患者可通过该平台联系独立医疗提供者、开处方,并由第三方线上药房将该公司部分药品(如代谢、肥胖、偏头痛药物)直接配送到家。

LillyDirect 最初只是一次偶然的尝试,通过与 Stripe 等支付公司的合作,公司得以直接与用户建立数字联系,从而绕过复杂的渠道障碍,直接解决患者需求。平台的初衷是让需要胰岛素的患者以更低价格获得药物,随后才逐渐扩展到偏头痛等其他产品。
虽然公司内部起初对 DTC 模式存疑,担心会遭到大型药房反对,且公司本身也缺乏药房运营经验,但两件事促成了这一转向:
1. 市场正在加速数字化,消费者沟通方式不断变化;
2. 一家大型 PBM 因利润不足拒绝销售礼来的低价胰岛素,使公司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中间商。
DTC 模式的可行性来自治疗指数(TI)的扩大,GLP-1 的良好安全性则让患者可以自行判断需求,无需医生确认自己是否超重或肥胖。这也是 LillyDirect 真正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自费模式让患者可以避开传统体系,直接获得治疗。
治疗指数(Therapeutic Index,TI)是指药物产生有效治疗作用所需的剂量与产生毒性或不良反应所需的剂量之间的比率。简而言之,TI 越高表示药物使用越安全,因为治疗剂量与可能产生毒性的剂量之间差距更大。
平台的迅速增长还受益于 Zepbound 的推出。它的“诊断”条件极其简单:只需要一台体重秤,再加上公司提供的大规模远程医疗服务,并将部分流程外包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协助患者选择正确治疗方案。如今,LillyDirect 的年收入已达数十亿美元,成为最成功的在线处方平台之一。
这一成功表明,与终端用户建立直接而稳固的关系能够显著提高效率与价值。尽管医疗行业受到实体店和州级监管的限制,数字直连患者的趋势仍然不可逆转。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解析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04.
美国医疗生态问题
私人医疗系统的扭曲
与许多国家公共资助的系统不同,美国拥有一个高度市场化、效率较高的私人医疗系统,但“提供最好的服务并据此收费”的理念也带来了结构性扭曲:这个理念在许多常见疾病的医疗流程被过度应用,导致初级护理机构不断追求不必要的高端化,反而让简单的诊疗变得昂贵而复杂。因此,尽管私人医疗系统的效率较高,美国人对私人化医疗的总体态度却偏向负面。
慢性病带来的资金错配
美国医疗与科研的资金架构建立在传统的“急性病时代”,但如今约 70% 的医疗支出来自慢性病管理,这需要患者长期行为改变,医生要持续随访。但现有医疗支付体系不仅无法支持这种长期管理,还意外形成了一个道德风险结构:覆盖范围越广的系统,反而越需要为行为最差的患者投入更多资源。
仿制药的效果偏差和供应风险
美国的仿制药是 OECD 国家中最发达且最便宜的,这带来了显著的积极效果:大量有效药物能够以极低成本被广泛使用,例如百忧解等药物每天只需 3 美分。这一体系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政策重大调整,当时为了让仿制药能在专利到期后更容易进入市场,美国政府建立了结构化的专利诉讼路径。
美国政府于 1984 年通过 Hatch–Waxman 法案,确立了仿制药在原专利到期后更快进入市场的法规路径,包括创建“简化仿制药申请(ANDA)” 路径、允许仿制药厂商在专利到期前提前准备申报材料,并设立专利诉讼机制以及 180 天首次仿制药的市场独占期。该法案为仿制药市场提供了更高的可预测性,从而加速了仿制药的上市进程。
然而,仿制药在实际使用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偏差:
1. 5% 规则:活性成分允许存在 ±5% 的差异,对于剂量敏感人群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
2. 赋形剂(excipients): 药片中的缓冲化合物等成分会影响吸收率。
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可能导致仿制药与品牌药在部分人群中出现不同效果。但小分子化学仿制药无需展示疗效(efficacy)证明,只需通过药代动力学(PK)测试和吸收实验(Absorption Study)即可上市。
药代动力学(PK)测试是测量药物在人体内如何被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ADME)的过程,用来判断仿制药与原研药在体内“表现”是否一致。
吸收实验是 PK 的一个关键部分,指测量药物进入血液的速度和程度,是判断两种药是否“生物等效”的核心指标。
此外,仿制药行业历史上也出现过欺诈案例,例如印度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商曾因欺诈、伪造或滥用生物相似性分析而支付巨额罚款。许多患者在从品牌药切换到仿制药后也表示主观体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表明仿制药在主观感受上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品牌药。
最后,在长期追求低成本的压力下,仿制药制造几乎全面转移到东欧、印度、中国等海外化工厂。然而,由于仿制药的生产工艺复杂,过度压价容易引发质量问题,甚至出现注射用仿制药的供应短缺。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Dave 认为,对于缺乏疗效验证的剂量敏感性药物,需要建立相应标记方法,使监管机构能够进行分级判断,而且美国应为供应弹性支付溢价,但目前尚未实现。

05.
药物研发领域存在的挑战
监管要求日益严苛
Paul Janssen 曾发现约 80 种获批药物,被视为医学界的 MVP。他曾指出,新药从发现到商业化的开发周期已经从 1953 年时的一两年,延长到如今约 12 年,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他认为,这一变化并非科学本身的需要,而是大量资源被浪费在当局强加的、与医学研究关系不大的测试上,如果没有这些额外要求,新药开发时间可以不需要这么漫长。
但这种官僚化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在面对过往药物事故时不断作出“更严格监管”选择的结果。全球目前只有约 2000 种人造获批药物,但每当出现真实或被怀疑的问题的时候,各国监管体系都会进一步干预,要求更多信息或重新平衡风险收益,这导致法规只增不减,从未被取消,为后续成本更低的项目设置了更高的准入门槛。
2004 年,默克的 Vioxx 和 GSK 的 Avandia 因电子记录提示可能存在心血管风险而先后撤市,并引发了数十亿美元的诉讼。然而,后续分析却显示,这些风险未必真实存在。但这一事件仍然促成了重要的监管转向:监管机构开始要求新药在获批上市前必须证明不存在心血管风险。

但心血管事件属于需长期观察的终点指标,意味着,新型糖尿病药物必须等待心血管事件在真实人群中自然发生,并积累到能够产生统计学差异的数量,导致药物开发周期被迫延长四至五年,显著推高了研发成本。
如今,tirzepatide 等肠促胰岛素药物已经展示出了明确的心血管益处,而计算技术的改进也明显提升了早期信号的识别能力。因此,在监管长期只增不减的背景下,Dave 认为重新评估政策要求并为预防性药物支付成本,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方向。
资本激励减弱
美国有全球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但每花 1 美元中只有 10 美分用于药物,其余 90 美分都花在治疗药物试图预防的疾病上。但事实上,自 1965 年 Medicare 和 Medicaid 设立以来,美国预期寿命已经延长了八年,其中有 5-6 年来自新药研发,因此更合理的做法应是让更多资源流向创新研究。
然而,为研发提供资金的私人市场正面临信心下滑。因为资本在价格稳定、回报期更长的环境下更愿意投入,但现实情况却相反:一方面,新药审批周期越来越长,使得专利期实际上被缩短;另一方面,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IRA)允许政府在上市约七年后介入定价,显著削弱了企业收回成本的能力。这双重影响使得大型制药公司的市盈率被压缩至 20 年来低点,生物技术行业的融资环境也因此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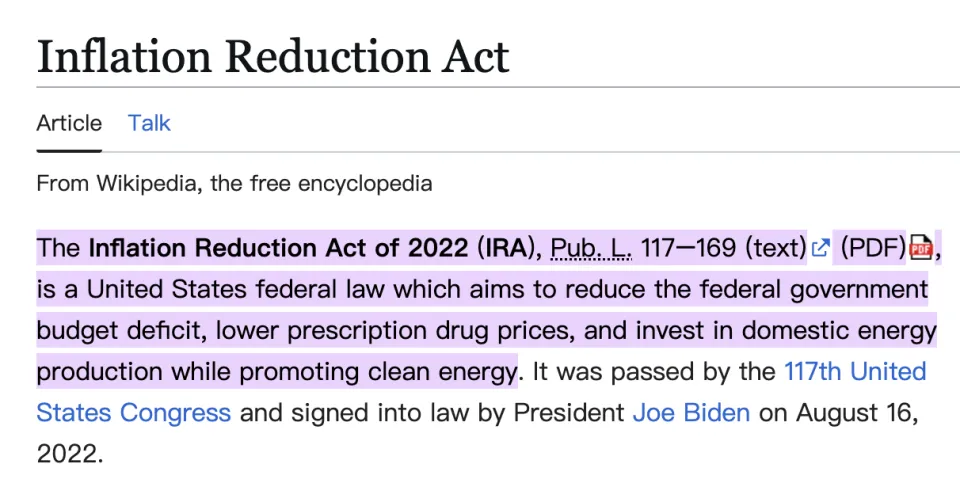
在这种背景下,延长专利期限虽然能提升药企回报,但竞争格局的影响更为关键:大多数药物类别中,很少只剩下单一产品。以 GLP‑1 药物为例,目前市面上仅有两种上市药物,但全球研发管线可能多达 80 种。一旦两三种新药进入同一治疗领域,除非具备明显优势,后进入者很难获得市场份额。此外,当专利到期后,仿制药的上市通常会导致品牌药当天失去约 97% 的定价能力。
专利跨国保护难度增加
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药物管线中的份额从几乎为零增长到约 30%,主要集中在迭代式衍生品的开发,中国正在迅速积累经验,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此,有人担心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可能会像电子制造业一样逐步向中国转移。
而且,生物技术领域还涌现出了大量来自美国境外的“克隆”式专利:企业仅通过极其细微、几乎不改变功能的结构改动,就能重新申请专利,形成一种“影子仿制药”体系。这类“微调复制”正在削弱既有的专利框架。毕竟,美国在 2011 年改革专利制度的本意是鼓励研究者尽早申报以换取垄断期,但如果竞争者能借助微小化学结构变动轻易规避既有专利,这种垄断激励就会被稀释。
2011 年,美国通过 America Invents Act,该法将美国的专利制度由“先发明”(first-to-invent)改为“先申请”(first-inventor-to-file),也就是专利权优先授予最先递交申请的人,而不再看谁最早发明。
Dave 强调,生物制药是知识经济的尖端产业,美国必须保留本土的生物制药产业,因为这一产业不仅能创造高薪与巨大经济产出,还能带动相关制造业形成区域集群效应,使经济活力从高价值产业中心持续扩散到供应链与当地社区,带来更广泛的就业与增长。同时,保留本土的生物制药能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类似 COVID-19 的危机中,美国需要具备独立生产关键药物的能力。
进一步,Dave 认为如果美国希望建立更“美国优先”的专利保护体系,可以考虑两项措施:
1. 提供数据保护期:给予独立于专利的 12 年数据保护期,保障创新者对昂贵的原始临床数据(例如可能高达 30 亿美元的三期临床投入)拥有排他权,避免“克隆者”不承担成本却能抢先申请专利。
2. 延长保密期:在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联盟中,将保密期延长至超过专利审查期,例如延长到六年,以确保产品在进入临床阶段后不易被快速复制,即便复制方在中国启动项目也难以对市场造成影响。
药品定价失衡
• 高标价、低净价
美国药物的公开标价与各方最终支付的实际价格之间往往差距巨大,而药企能提供的最低净价又受到 Medicaid 最优惠价格机制的限制,这导致大型保险公司能够获得接近政府水平的低价优惠,而规模较小的机构则越来越难以争取到同等折扣。
Medicaid 是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项目,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保障,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资助和管理。Medicaid 最优惠价格机制要求药企必须把自己在市场上给出的最低实际成交价同步提供给 Medicaid,因此药企不敢随便把价格压得太低给其他买家。
导致价差扩大的原因之一是中间商的错误激励:药物福利管理机构(PBMs)和团体采购组织等中间商通过“按标价折扣百分比”获取回报,导致标价越高,他们获利越多,这使得制造商不再聚焦于药物的真实临床价值,而是转向如何制造更大的标价净价差。
比如胰岛素标价高达 275 美元,制造商真正拿到的净价仅约 30–40 美元,巨大的差价主要被中间商获取,最终的受害者是无保险的现金支付患者,因为他们必须支付高昂标价。
此外,由于药物的生产成本相对低,而主要成本集中在研发上,美国实际上承担了全球大部分药物研发支出。同时,许多国家都以极低价格采购药物。这种国际价格差在美国国内激化了公众情绪,使高药价被视为价格欺诈。
在 Dave 看来,健康具有社会属性,不同于普通商品,应建立单一价格体系,并由真正独立的中间商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中间商应基于全量的索赔记录评估用药情况、风险与收益并制定价格;如果研究结果出乎意料且显示收益显著,制造商应当被允许获得更高的价格。这种机制能够激励企业投入更高风险、潜在价值更大的适应症,而不是将资源耗费在商业谈判上,在专利期将尽时又被迫迅速开发下一个药物。
• 价格不透明
美国药品定价失衡另一个表现是价格高度不透明:虽然药品的标价可以查到,但其余约 90% 的医疗服务价格几乎从未在使用前对患者公开,导致消费者在获得医疗服务时处于“盲买”状态。而且,为改善透明度而出台的法规几乎都失败了:遵守者极少,即便遵守,也只是将高度编码、消费者难以理解的价格数据库放在晦涩的网站上,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同时,联邦规定要根据护理地点设置差异化支付,这进一步扭曲了价格结构:成本更低的门诊诊所反而被“惩罚”,而更昂贵的大型医院体系却获得更高的支付。例如,在医院内部实验室做一次抽血的价格可能高达 650 美元,却没有人提出质疑,就是因为患者并不知道真实费用,他们几乎无法像在其他消费领域那样做出基于价格的理性判断。
• 传统定价模式不适应新疗法
传统药物的商业模式有点像“收缩包装软件”(shrink wrap software):公司把产品做出来、交付出去,所有价值都必须在那张发票上一次性体现。这种方式对长期使用传统药物的患者还算合理,但对于基因治疗这种只需一次给药,却可能带来长期疗效的疗法就不再适用。
因此,定价方式必须创新。以礼来正在研发的 PCSK9 一次性编辑疗法为例,理论上通过一次治疗就可以长期降低 LDL,从而替代每年数千美元的常规药物。然而,现行的“按单位收费”(unit pricing model)的定价模式无法充分体现这种一次性疗法的全部价值。
目前,基因疗法缺乏适合的定价机制,核心障碍出现在支付端,尤其是政府支付体系的僵化。政府的规则仍基于“购买一个单位、支付一笔费用”的传统逻辑,但基因疗法更需要类似 SaaS 的许可模式:企业可以根据疗效在未来持续获得报酬,而如果疗效不达标则停止收费。要让基因疗法在常见疾病中普及,就必须解决这种价值认知与单位定价模式之间的根本矛盾。

美国细胞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06.
临床试验的主要难点
试验成本昂贵
目前,临床试验中每位受试者的成本中位数已超过 4 万美元,并以每年约 7%–8% 的速度上涨,与整体医疗系统的成本增长幅度相当。这背后的原因在于:
1. 临床试验往往需要招募病情最复杂、医疗花费最高的患者群体。为了确保所有受试者接受统一且充分的护理,公司必须承担相当一部分医疗系统的运行成本,以避免依赖不同医生各自差异较大的日常治疗方案。
2. 试验费用中还有一部分用于向研究机构支付溢价,来覆盖研究人员投入的时间及各类运营管理成本。通常,这个费用会比常规医疗支出高出 20%–30%,因为试验要求更高质量的护理、更密集的检测以及更多随访。

临床试验阶段
参与试验的患者数量少
在美国,只有约 4% 的癌症患者参与临床试验,而在西班牙和澳大利亚,这一比例超过 25%。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
1. 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临床试验流程有更好的系统化管理,使患者招募和试验运行更加顺畅。
2. 一些国家的常规医疗质量可能不如美国,因此患者和医生更愿意通过参与试验来获得更优质的护理。
3. 美国的医疗体系较为分散,每个开展试验的机构都需要单独获得审批(IRB),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则采用统一的审批系统,使试验启动速度更快。
以礼来为例,礼来的临床研发周期通常不到七年,但其中约有一半时间都花费在了患者招募上。即便试验方案已开放、站点完成培训,公司仍需要长期等待患者主动前来报名。
为缓解这一瓶颈,礼来开始尝试更主动的招募方式,比如从现有数据库中筛选可能符合试验条件的患者并直接联系他们。因为许多患者本身比他们的医生或所在机构更愿意参与试验,直接沟通能提高招募效率。但这项工作高度依赖电子健康记录,但相关数据往往分散且质量参差,因此优化数据整理至关重要。
理想的方向是推动更远程化、更高效的试验模式。例如,在阿尔茨海默病预防研究中,美国的团队通过大规模筛查超过 8 万名参与者,实现了史上最快的入组速度。受试者只需一次远程访视,通过血液检测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 PET 扫描,从而决定是否正式入组。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预防性药物试验,因为这类参与者通常是关注自身健康的中年人,他们愿意投入时间,也有能力参与,并希望预防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严重的疾病。这类方法为未来的临床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PET 扫描(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是一种利用放射性示踪剂来显示体内代谢与功能活动的医学影像技术,可帮助医生观察器官是否正常工作。
Reference
Dave Ricks, CEO of Eli Lilly, on GLP-1s and the business of pharma|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VCDx_kFw&t=1s
排版:夏悦涵